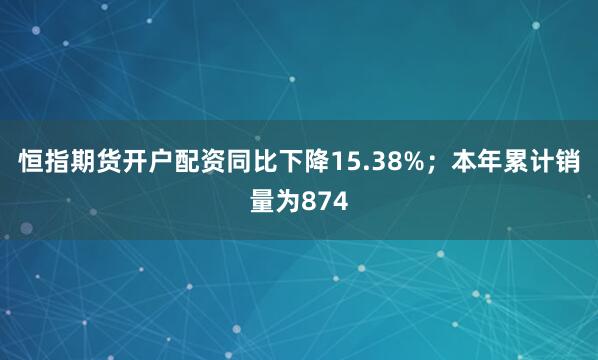“世上没有后悔药”—— 这句俗语,在张申府晚年的无数个黄昏里,总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。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元老、曾推荐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的哲学家,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 1925 年的那个决定较劲:因政治意见不合,他毅然退出了亲手参与创建的政党。直到暮年,当他独自蜷缩在图书馆的旧书堆里,才终于看清那份冲动背后的代价。
从书香世家到建党核心:一位哲学家的革命起步
1893 年,张申府出生于河北献县的官宦世家。祖父曾官至翰林院编修,父亲是国会议员,家中藏书万卷,自幼浸润在 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 的传统里。但这位世家子弟却不走寻常路:别人埋首经史子集,他却痴迷数理与哲学;别人追求科举功名,他却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,一头扎进了 “德先生” 与 “赛先生” 的世界。
1914 年,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,师从哲学家梁漱溟,后留校担任助教。在北大,他遇到了李大钊、陈独秀 —— 两位正在点燃中国革命火种的先驱。彼时,《新青年》激荡思想,五四运动席卷全国,张申府被 “改造社会” 的理想深深吸引。他与李大钊、陈独秀共同创办《每周评论》,笔锋锐利地抨击时弊,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。
1920 年,当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时,张申府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。他与李大钊在北大秘密讨论建党纲领,起草早期文件,甚至在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前,就已在欧洲发展党员 —— 这使他成为少数同时参与国内建党与欧洲共产主义活动的元老。
展开剩余80%在巴黎留学期间,28 岁的张申府遇到了 22 岁的周恩来。彼时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国,怀抱 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 的理想,在欧洲组织进步学生活动。张申府看出这个年轻人的锋芒,主动与他深谈,向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。1922 年,经张申府介绍,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成员。
1924 年黄埔军校成立,孙中山急需优秀人才主持政治部工作。张申府向孙中山、蒋介石力荐周恩来:“此人有雄才,懂军事,更懂人心,能担此任。” 正是这一推荐,让周恩来踏上了军事舞台,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埋下伏笔。此时的张申府,既是哲学家,也是革命的 “伯乐”,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,意气风发。
因政见决裂:一位理想主义者的 “决绝转身”
1925 年,一场关于 “国共合作” 的争论,成了张申府人生的分水岭。
当时,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展开更深入的合作,甚至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。这一决策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,张申府是坚定的反对者。
他的理由带着哲学家的执拗:“国民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政党,与我们的理想根本对立。合作会模糊我们的立场,最终被同化。” 尤其让他不满的是蒋介石的专断 —— 此前他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,因看不惯蒋介石排斥共产党人的做法,早已愤然离职。
争论升级到白热化。在一次中央会议上,张申府与蔡和森等同志激烈争执,拍着桌子喊道:“如果坚持与国民党妥协,我就退出!” 同志们以为他只是气话,劝他 “冷静下来再谈”,但这位信奉 “要么纯粹,要么离开” 的哲学家,竟真的递交了退党申请。
这一举动在党内引起震动。李大钊亲自找他谈话:“申府,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哪能事事如意?暂时妥协是为了长远目标。” 张申府却摇头:“我的理想里,没有‘暂时妥协’的位置。” 1925 年,他正式退出中国共产党,成为中共历史上最早退党的创党元老之一。
多年后,有人问他当时为何如此决绝,他苦笑:“那时太年轻,把政治当成了哲学命题 —— 非黑即白,不懂灰度。”
退党后的人生:从政治舞台到学术象牙塔
退党后的张申府,并未沉寂。他转身投入学术研究,在哲学与数学领域开辟了新天地。
他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罗素哲学的学者,著有《罗素哲学译述》《唯物辩证法论战》等著作,将西方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比研究,提出 “解析唯物论” 的观点,在学术界独树一帜。钱钟书曾坦言:“我对哲学的兴趣,最初就来自张申府先生的文章。” 他还参与创办《清华学报》《新建设》等刊物,成为文化界的重要声音。
但他始终没能完全脱离政治。1936 年,他参与发起 “文化界救国会”,呼吁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,与宋庆龄、沈钧儒等共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抗战期间,他在重庆担任民盟中央常委,为团结民主力量奔走。但当蒋介石邀请他担任参政员时,他再次拒绝:“我不会为独裁者站台。” 这份不妥协的脾气,与他当年退党时如出一辙。
1948 年,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,张申府却发表了《呼吁和平》一文,主张 “国共划江而治”。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,连妻子刘清扬(早期共产党员)都与他激烈争执,最终两人离婚。此后,他彻底淡出政治,搬进北京图书馆的一间小屋,终日与旧书为伴。
晚年的悔恨:“我错了,可回不去了”
1970 年代末,已是耄耋老人的张申府,身体日渐衰弱,却总爱坐在图书馆的窗边,望着外面的红旗发呆。有晚辈问他:“先生这辈子,最遗憾的事是什么?” 他沉默良久,才颤巍巍地说:“1925 年,我不该退党。”
他开始翻看早年的日记,那些与李大钊讨论建党纲领的夜晚,与周恩来在巴黎街头畅谈革命的清晨,在黄埔军校为周恩来铺路的细节…… 一幕幕涌上心头。他曾对友人叹息:“那时总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,容不得半点不同。可革命哪有纯粹的‘真理’?都是在妥协中前进的。我太骄傲了。”
他的悔恨并非出于对名利的惋惜 —— 退党后他从未抱怨过生活的清苦,而是源于对理想的愧疚。“我参与创建了党,却在它最需要团结的时候离开了。” 这份愧疚,成了他晚年无法卸下的重担。
1986 年 6 月 20 日,张申府在北京逝世,享年 93 岁。整理遗物时,人们发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泛黄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扉页上有他晚年写的一行小字:“大道之行,殊途同归。我走岔了,可方向没错。”
历史的回响:一位 “异类” 元老的启示
张申府的一生,像一面镜子,照见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,个人与历史的纠缠。
他是学者中的革命者,用哲学思维解构旧世界,却在政治实操中栽了跟头;他是革命者中的学者,坚守理想的纯粹,却不懂革命需要必要的妥协。他推荐周恩来,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关键人才;他因政见退党,成为自己人生的 “缺憾”。
有人说他 “固执”,有人说他 “天真”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始终在追求自己认定的 “真理”—— 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救亡图存,还是晚年的学术坚守。他的悔恨,恰恰证明了他对理想的真诚:若非深爱,何来痛悔?
如今,当我们回望这位创党元老的一生,或许能读懂: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剧本,每个选择都带着时代的烙印;理想的实现,既要坚守初心,也要懂得在复杂现实中寻找前行的路径。而 “没有后悔药” 的遗憾,更提醒我们:每个选择都应既忠于内心,也敬畏历史。
张申府的名字,或许不如李大钊、周恩来响亮,但他的故事,却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:革命不仅是英雄的传奇,也是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抉择。而那些 “错了” 的选择,与 “对了” 的坚持一样,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发布于:河北省炒股配资平台大全,炒股配资公司,大额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